- 近期网站停站换新具体说明
- 按以上说明时间,延期一周至网站时间26-27左右。具体实施前两天会在此提前通知具体实施时间
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4. 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
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执政党实现自己的承诺,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将过去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上的土地分给了其他农民。这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在土地所有权上一次最伟大的变革,给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1950-1952年,粮食总产和亩产分别提高14%和10.5%。这个增长,主要得自于由战乱而进入了和平建设环境,个体农民和国营农场新开垦了八千万亩耕地(占总耕地6%)以及这几年良好的气候条件,当然也与新分得土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关。1953-1957年,互助组和合作社(包括低级社和高级社)在农村得到普遍实行,复种指数大幅提高,粮食总产和亩产分别增长20.6%和27%,亩产年递增率是4.8%,这个时期的集体化与执政党的组织和引导有很大的关系,但基本实行了农民自愿加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
解放后,虽然农民分得了土地,但各农户的劳动力和拥有的生产资料像农具牲畜等是不平衡的,相应的,生产结果就有差别。由此产生了贫富分化,甚至出现了卖地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像河北西铺的王国藩,山西大寨的陈永贵等,把那些处于相对贫弱的农户组织起来,实行生产上的互助。由于这种做法带来了增产的效果,单干户在看到此优越性后也自愿加入进来,加上政府的引导和促进,全国就开始了普遍的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在粮食亩产达到一定程度后,要继续提高,就必须在土地的改造和水利灌溉的建设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进行更大规模的合作,这些客观要求促成了集体化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1958年一些人民公社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前几年合作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仅从新修水利就可以看到这种集体合作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变化。1950年,全国的灌溉面积只有二千万公顷,而到了1958年,就增加到了三千多万公顷。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在组织起来后,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就获得了过去几千年努力成果的一半多。
但是如此快速以及大规模的集体化,对于一个有着几千年个体生产的国度来说,无论是各级政府的推动者和领导者,还是普通农民,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面前都产生了混乱和不适应,并由此而付出了极大代价。在经过1959–1961三年粮食大减产后,1965年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1965至1979年公社解体, 这十四年的粮食亩产年递增率是4.5%,与50年代相当,而1980开始实行分田到户后至1998年,粮食亩产递增率是2.9%,增速明显下落,其背后的原因将在后面进行分析。
其实,粮食产量的这些变化,基本上都可以从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和技术进步上获得解释,如本文第三章所述。但经济学专业的林毅夫却总是企图从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上去找原因,往往就在数据采样和处理上表现出个人的一厢情愿。
林毅夫在1990年写出本文第二章分析过的《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一文,提出“博弈论”之前两年,就发表了《中国农业家庭责任制改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一文,企图建立起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个体劳动者的激励要高于集体劳动者,然后以经验数据加以证明。
林的理论模型旨在说明,对于个人的劳动激励来说,生产队体制低于家庭承包制,因为前者要付出对个人劳动的监督成本,故不能实行完全的监督,而后者根本就无须监督。对此笔者有两点异议:1)林没有给出什么是完全监督的标准。以笔者的亲身体验,在生产队体制下,大家一起劳动,并定期对每个劳动者的工分进行民主评议,就是一种有效的反馈和监督形式。2)林假定家庭承包制下只有一个劳动者,因此是完全的自我激励,无须监督,是不成立的。农村中的家庭,大多数都有一个以上的劳动者,虽然规模更小,按林的理论,也应存在所谓激励与监督的问题。
林毅夫也考虑到,集体劳动和个体劳动的效率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中设定了一个规模效应系数来对两者的效益加以区分,并导出,只要这个系数不大于2,那么个体劳动的效益就总是高于集体劳动。问题在于,理论和实践上这个系数都可以是大于2的。至少,林毅夫会承认,50年代时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效益就大于当时的个体劳动。连带的问题是,为什么生产队解体后,农民没有“理性”地回到互助组和合作社呢?要作出不违反理性人假设的回答,似乎只能说他们是被强制的,可是这与林毅夫后面的论述又是矛盾的。
当然,笔者认为用这种数学模型来描述农民劳动时偷懒不偷懒的问题,根本就是学者们关在书斋里为写文章而做的伪学问,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那些终生在黄土地黑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会在心里盘算自己理应付出的劳动也许只能换回1/N的边际效益后而选择偷懒的“理性人”,如果说绝对没有可能太武断,但说少之又少却不会错。个别偷懒的人,在集体劳动的情况下,一般也会在受到公众的议论后而有所改正,因为人都是有自尊的。而且,在集体劳动的环境下,男人和女人,青年和中年,大家因交往而获得的愉悦,无论是对个人身心健康还是对劳动质量而言,都有正面的作用。相反,一个人如果成天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孤独地干活,长时间下来,其精神状态不可能十分高昂。另外,集体制下的分工合作,可以做到人尽其才,使那些有特殊专长者的效用得到最大发挥。这些差别,是林的数学模型所无法算计的。同时,农民在组织起来后共同向自然挑战所具有的规模效应,很难用一个什么系数来定量描述。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农民在改良土壤,新修水利这两项对农业生产影响至巨的事业上所显示出的伟力,与中国此前和此后以及印度的个体农民相比,就是很好的证明。
林毅夫的那个数学模型,是不可能由经验数据获得验证的,因为他所定义的那些自变量,根本就找不到经验数据。但林毅夫还是另辟蹊径,从中国1980至1982年向家庭承包制转换的过程中找出了一些因变量和自变量以及相关数据,以回归分析来构筑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然而,这些回归方程与他前面建立的理论模型并没多大联系,而且几乎什么也说明不了。
比如,林毅夫以生产队的劳动者数量,种植业与畜牧业总产值的比率,农业机械的马力数,以及耕畜量作自变量,来说明这些因素对因变量即家庭承包制的实现率的影响,符合他前面建立的理论模型的预期。且不说因变量是否真的与这些自变量线性相关,起码因变量,即家庭责任制的转变必须是一个自然(自发自愿)的过程才有意义。但这个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自然发生而是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的。作为这个制度推动者的万里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就坦诚地说,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区市中,最初只有三个省区的领导人采取拥护的态度(老田:“农村政绩工程”与“杜润生-林毅夫假设”)。这么说,并不否认全国各地,从各级干部到农民,都存在有分田单干的想法和要求,但林文不加区分,按省区市这样大的区域来采样,然后以两年之间的一次变化量作输出变量就进行回归分析,这么草率粗糙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怎么可能客观可信呢。
林还建立了其它一些回归方程,但都没有公布变量的采样值,也没有采样值与回归预测值之间的比较,R平方或调整R平方都不高(其中有两个方程的调整R平方分别是0.05和0.07),可信度极低,笔者无法予以评论,但须指出以下两点:
1)林试图证明包产到户促进了化肥施用量的提高,是他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想当然。80年代初,中国的化肥施用量还处在较低的水平,主要是生产能力不够。在此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化肥施用量的增加仅意味着化肥产量提高了,生产出多少就能销售多少,把它和分田到户以及农民的积极性扯在一起是无稽之谈。
2)林以包产到户后那几年劳动量增加了15%作为农民的积极性提高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这里面既有人口自然增加的因素,也与劳动效率下降有关。包产到户使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受到损害(润树: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的一点回顾与分析,2008),有些农户连耕畜都没有或用不上,不得不靠劳动量的增加来加以补偿(有些当年在农村生活的网友披露,他们在十一二岁就被推上了生产第一线)。即使这样,劳动力依然紧张,那几年复种指数下降了4个百分点,就是一个佐证。
1992年,林毅夫又发表了“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一文,试图以Griliches(1963)年提出的生产函数法来评估和验证各项农业改革对农业增长的影响。表4.1列出了林文的生产函数分析所依据的因变量(产出)和自变量样本。
表4.1 林毅夫分析农业产值增长用到的采样数据

表中各变量的含义是:
产出 – 种植业总产值,劳动- 投入种植业的劳动力,耕地 - 种植业的播种面积,资本- 资本投入,化肥 - 化肥使用量,承包- 家庭承包实现率,价比1 - 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与投入价格的比率,价比2 – 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与投入价格的比率,其它- 用于非粮食生产的耕地百分比,复种 – 复种指数,趋势 - 时间变化量,函盖随时间进步的技术性变量。这些变量中,除承包,其它,复种和趋势外,所有变量都是以1980年为基数(100%)的百分比指数。
林对这些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自1979年开始的由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是1978- 1984年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该段时期的主要农作物产值增长了42.23%,其中近一半应归于农作制度的转变。这么大的增长是十分惊人的,令许多人把它当作定论,从而对分田单干的制度改革大加礼赞。以下是林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原文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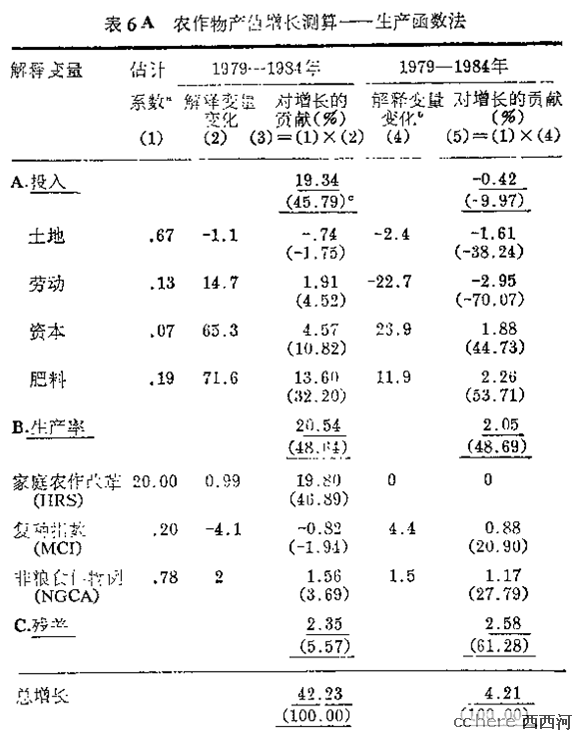
图4.1 林毅夫的回归分析结果
这个数字看上去很漂亮,听起来也很悦耳,然而里面的内涵不是那么实在。首先,笔者将林毅夫所给出的全部采样值输入统计学软件Minitab后,按他的模型结构进行回归计算,却根本不能获得他所给出的结果。此种回归分析,常常由于自变量的共线性(co-linearity),在自变量的不同组合下计算出差异很大的结果。统计学上“数据既会告诉真相,也会骗人”之说,在这里非常适用。其次,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被忽略了,比如土地的变化,杂交水稻和小麦在70年代末的普遍推广,以及气候,等等。笔者将这些变量加入林的模型后,获得的结果就大不一样。但是,在如此多的影响因素下,笔者没有林毅夫那样的自信,将这些回归结果轻率地拿来做判断一个制度变革带来的效应这样的大事的依据。然而,根据我们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来进行分析,完全可以得出比计算机进行的回归分析可靠得多的结果。
表4.2 1969–1989 年粮食产量及相关数据

林毅夫把78和79年算在农作制度改革期内是取巧的做法。虽然这两年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增长,但都还是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体制,不应把它们算在家庭承包制的帐上。去除这两年后,1980至1984这五年的增长就是34.8%,而不是42.23%。这个增长仍然是十分可观的,特别是82,83和84年。那么,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应归于家庭承包制下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长呢?
积极性是不能测量的,答案还是要从土肥水土这些主要的增长源泉中去找。下面来做一个简单的减法计算,将以下因素带来的增长从中扣除:
1)平均增长,即不实行家庭承包制也可以得到的增长 - 此前十年(1970- 1979)共增长了30%,取其一半(五年)即15%。
2)土地 - 农民的自留地在集体制时期占生产队耕地的5 – 7%,另外有些地方还给私人留出了饲料地,山坡林地等,加起来高达集体耕地的10-15%。农民对自留地的利用率很高,复种指数可达300%,既种蔬菜,也种粮食和经济作物。这一项在集体制时是没有计入产值的,但承包以后就计入了。考虑到这些土地种的蔬菜在承包期也未计入产值,以及有些地方在此之前就已收回了自留地,取4%应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3)肥料 - 化肥的施用量在78-84年间从3.59公斤/亩提高到了10.27公斤/亩,增长了190%,是70-77年增长的两倍多。如果按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占50%的保守估计,80-84年由于化肥的增长至少应在原有增长基础上加3个百分点(参考本文3.3)。
4)良种 - 杂交水稻和小麦良种的普遍推广,应使这几年的粮食增产比以前更快,算2个百分点应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参考本文3.4)。
5)气候 – 1984年的受灾面积相对于耕地面积比1979年低5.6%,但成灾面积高0.84%,综合计算大约有1个百分点的差别。
以上四个因素加起来,共使产出增加25%,这样就只留下约10%的增长可能源于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但这还是不具有说服力,除非能够将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体现在种庄稼的具体操作上,比如多施肥,多浇水,多松土,多除草等。这样做的效果应该不但在农业产值,而且在粮食产量上也显示出来。但对比1984年和1979年的粮食产量,增长却只有22.6%。既然农业产值是按可比价算的,那么多出来的12.2%的增长就只能来自非粮食生产的增长了。仔细检查这两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分布和产出就可以发现,1984年的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较1979年多出了6800万亩,增长约30%,而大豆,棉花,油料,糖料,麻类,烟叶等经济作物也确实都呈大幅度增长。那么,这12.2%的产值增长源自于这些经济作物是没有疑问的。林毅夫的研究中也考虑了这个因素,以非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与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的比率作为回归分析的自变量(表4.1中的“其它”)。但是他的分析结果却只将1.56%的增长给了这个变量,太吝啬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回归分析的结果往往是很不可靠的。
如此一来,实行家庭承包制实行之后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对农业的的增长就什么也看不到了,而且还欠着点。如果有人硬要说由经济作物带来的那12.2%的增长应归于家庭承包制,笔者也不作争议,但须指出,当粮食产量达到相当高度以后,必然导致部分耕地转到经济作物的生产,不管是集体制还是承包制,因为那样同样符合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设。公道地说,那几年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一定是很高的,劳动量更大(增加15%,尚不包括童工),劳动时间可能也更长,只是这些劳动都用来补偿由于农业机械的废置以及分工合作的丧失所造成的劳动效率下降了。
其实,如果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而把眼界放宽到一个相对长一点的时段,就可以轻易打破所谓分田单干的“积极性”神话。1969-1979年集体制时期的粮食亩产增长了66%,1979-1989年分田单干时期只增长了34%,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前一个时期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比后一个时期高32%呢?显然不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来分析事物的变化发展的原因,总是着眼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虽然也不忽视外部条件的作用),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归之于不可解释的精神现象。这不是说生产者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不重要,而是说这个积极性,即精神现象,必须在能够影响粮食生产的物质条件上表现出来,是可以认识的。林毅夫找到了那几年农业产值增长的部分因素,然后将自己无法解释的部分增长归之于积极性,是省事和武断的做法。当然,笔者以上的减法计算必然有误差,或正或负。如果实际结果仍然存在未解释的增长,那么也许可以说,承包制后农民的积极性还发挥在了多浇水,多施肥(未计入统计),多松土,多除草上面,等等。即便如此,由此带来的增长贡献也不可能有林毅夫计算的那么高。而真实情况也可能相反,由于效率下降导致劳动力紧张,他们基本上不能分出余力多干那些活,否则,为什么不在产出效率更高的复种指数上下功夫呢?
下面,进一步分析计算家庭承包制给中国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害。本文3.2中提到,1977至1989年的13年间,灌溉面积没有丝毫增长,加上分田到户后农田基本建设停顿,水库失修以及灌溉系统的利用率降低,使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下降。1980至1998年的平均成灾面积是耕地面积的20.2%,比此前30年的平均值10.8%高了近一倍,而非成灾面积也增加了4.6%(这里面不排除有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现在就来估算这个变化所造成的粮食减产。
按成灾面积亩产平均减少50%,非成灾面积减少15%的保守数值估计,1980至1998年各年度的粮食减产列表于下:
表4.3 1980 – 1998 年因成灾面积增大所造成的粮食减产

这十八年合计减产约4.17亿吨,差不多是1959-1961年大减产的3倍,平均每年减少粮食产量5.08%。这是分田单干后粮食亩产的逐年增长2.9%远低于集体制70年代5.2%的原因之一。这也说明,林毅夫所谓家庭承包制实行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转化成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的源泉。虽然这么大的损失没有造成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它对于中国农业发展走什么道路的选择,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
到目前为止,笔者只是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分析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而没有触及这个制度变化所带来的其它效应,因此无法对这一变化作出全面评价。下一章的总结与前瞻也将局限在这个范围内,这是需要事先预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