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网站停站换新具体说明
- 按以上说明时间,延期一周至网站时间26-27左右。具体实施前两天会在此提前通知具体实施时间
主题:【原创】兵临城下—西方对华战争的舆论准备(一):彭斯讲话 -- CHS1
【导读】
2019年1月,犹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他首先鼓吹了他提出的“开放社会”的构想,并警告了中国掌握了先进的信息技术之后对开放社会造成的威胁。他随后回顾了个人的亲身经历,尤其是通过“开放社会基金会”改变了苏联社会和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他还表达了对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中国内部势力合作,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尝试遭到了失败的遗憾。索罗斯随后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他列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对他巩固权力的成功,尤其是取消了两届任期的限制,表示了巨大的不安。索罗斯号召,“我们中那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必须共同努力,结成一个有效的联盟。我们的任务不能交由政府来替我们完成。”索罗斯还以一带一路的倡议为例,攻击中国的这一倡议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并对如何应对这一倡议,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促使中国发生经济衰退,以及“与其轻易放过中兴和华为,还不如对这些企业进行打压”。他最后对中国的商界和部分政治精英反对习近平寄予了厚望。
索罗斯的演讲发表于2019年初。从随后美国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的污蔑和制裁,以及蓬佩奥等政客的一系列反华演讲来看,这篇演讲不啻于索罗斯代表的国际金融势力的对华宣战书。
索罗斯演讲原文可见链接:https://www.georgesoros.com/2019/01/24/remarks-delivered-at-the-world-economic-foru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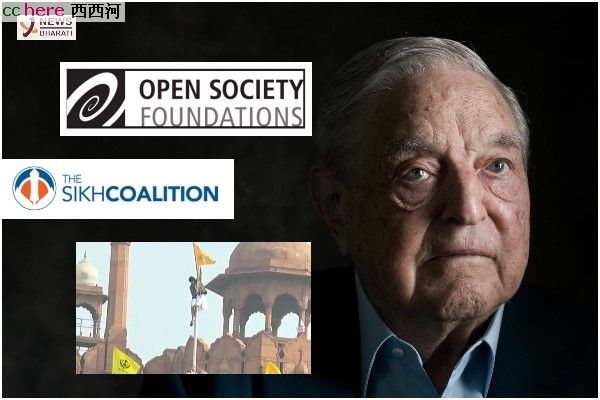
【译文】
瑞士达沃斯,2019年1月24日
晚上好,感谢各位的莅临。
今晚,我想向世界发出一个警告,开放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威胁。
去年我给各位演讲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分析信息技术(IT)垄断的黑暗面。我当时说:“集权国家和拥有海量数据的IT垄断企业之间正在结成联盟,将企业监视的新兴体系与已经在发展阶段且由国家掌控的监控体系结合在一起。这一联盟很可能诞生出一个连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都无法想象的极权主义控制的网络”。
而今晚,我想提醒大家意识到开放社会所面临的致命危险,这些危险来自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所赋予专制政权的控制工具。中国是我会谈论的重点,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求的是不可颠覆的一党制。
自去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在极权控制上会采取的样式。
所有快速增长的关于一个人的信息将被整合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从而创建一个“社会信用体系”。“基于这些数据,算法会对人们进行评估,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对中国这个一党制国家构成威胁。”人们将会据此被区别对待。
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运行起来,但它的发展方向已经显而易见。社会信用体系将以前无古人的方式使个人的命运服从于一党制国家的利益。
社会信用体系让我感到恐惧和厌恶。不幸的是,一些中国人却觉得这一体系很吸引人,因为它提供了目前还无法实现的信息和服务,还可以保护守法公民不受国家敌人的侵害。
中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威权国家,但毫无疑问,中国是最富有、最强大、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最发达的威权国家。这使得习近平成为那些信奉开放社会理念的人的大敌。但对手不止习一人。威权政权正在全世界扎根,一旦成功,威权将变成极权。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创始人,我毕生都在与极权的和极端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些意识形态大言不惭的宣称,目的正当即手段正当。我相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不会被永远压制。但我也认识到,开放社会所面临严峻的挑战。
让我感到尤其不安的是,人工智能开发出来的控制工具给威权体制带来了相对于开放社会的内在优势。对威权体制来说,控制工具是个有用的工具;而对于开放社会来说,这些工具却是致命的威胁。
我用“开放社会”代指一个由法治主导,而非个人统治的社会,国家的作用在于保护人权和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特别关注那些遭受歧视或被社会排斥的人,以及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
相反,威权政权竭尽所有的控制工具来保障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代价则是那些被他们剥削和镇压的人们。
如果这些新兴科技给威权政权提供了一种内嵌优势,开放的社会还怎么能够得到保护呢?这是我一直思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值得让所有愿意生活在开放社会中的人来思考。
开放社会需要对开发控制工具的公司进行监管,而威权政权却可以宣称这些公司是“国家龙头企业”。这就是一些中国国有企业能够追上乃至超越跨国巨头的原因。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应该担忧的唯一问题。例如,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续。但是,开放社会所面临的结构性劣势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想和你们分享我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想法。
我对这个问题的深切关注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1930年出生在匈牙利,我是一个犹太人。当纳粹占领匈牙利并开始将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的时候,我只有13岁。
我很幸运,因为我父亲深知纳粹政权的性质,他为所有家人和其他一些犹太人伪造了身份证件,还找了藏身之处。我们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
1944年是塑造我人生的一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当纳粹政权被苏联占领取代时,我尽快地离开了匈牙利,前往英国避难。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时,我在导师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下发展出了自己的概念框架。当我在金融市场找到一份工作时,这个框架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个框架与金融无关,但它立足于批判性思维。这让我能够分析指导机构投资者的流行理论的不足之处。我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并为自己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评论家而感到自豪。
经营一家对冲基金的压力巨大。当我赚到远超我自己或者我的家庭需要的金钱时,我进入了某种中年危机。为什么我要拼命来赚更多的钱?我对自己真正关心的事进行了漫长而深入的思考。1979年,我成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und)。我把它的目标定义为帮助开放封闭的社会,减少开放社会的缺陷,以及促进批判性思维。
我的第一次尝试是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随后,我把注意力转向打开苏联的体制。我与匈牙利科学院建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当时匈牙利科学院处于共产党控制之下,但匈共的代表私下里对我的努力表示同情。这一次尝试成功得出乎我的意料。我陷进了所谓的“政治慈善事业”。当时是1984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试图在匈牙利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复制我的成功。在苏维埃帝国,包括苏联本身,我的尝试都收效甚高。但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我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看上去大有可期。这一次尝试包括让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备受尊敬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和一个急于向匈牙利学习的新成立的中国智库团队进行了互访。
基于这一良好的开端,我向智库负责人陈一谘提出了在中国复制匈牙利模式的建议。陈得到了赵紫阳总理和他一心改革的秘书鲍彤的支持。
1986年10月,我们成立了名为“中国基金会”(China Fund )的合资企业。这是一个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机构的机构。理论上,中国基金会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鲍彤是中国基金会的负责人。但是,众多反对激进改革的人联合起来攻击他。他们声称我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并要求对内的安全机构对中国基金会进行调查。为了自保,赵紫阳用一名对外的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替掉了陈一谘。这两个组织是平等的,不能干涉对方事务。
我认可了这一调整,因为我对陈一谘将大量的资金授予自己研究所的成员感到恼火,而且我并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政治内讧。但中国基金会的申请者很快注意到,基金会被政治警察控制了,他们开始远离基金会。没有人有勇气向我解释原因。
最后,一位受基金会赞助的中国人冒着风险到纽约来找我,并告诉了我这件事的缘由。随后,赵紫阳被免职,我以此为由关闭了基金会。这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前夕,并让与基金会有关的人的历史中留下了“污点”。他们费了很大劲来洗刷自己的污名,最终他们也做到了。
现在回想起来,试图建立一个运作方式对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的基金会显然是一个错误。在那个时候,给予一笔捐款能在捐款人和受赠人之间创造一种相互的义务感,让他们有义务永远忠诚于对方。
历史就是这样。现在我来谈谈去年发生的事,其中一些让我颇为震惊。
当我第一次去中国时,我结识了许多身居高位的人,他们是开放社会原则的狂热信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被赶到乡下接受再教育,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不亚于我在匈牙利的经历。但他们幸存了下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独裁统治的受气包。
他们渴望了解卡尔·波普尔关于开放社会的思想。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概念令人向往,他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却与我的有出入。他们熟悉儒家传统,但在中国向来没有投票的传统。他们思维中的等级观念仍然没变,并且对高官显贵有一种内生的尊敬。但我却更主张平等,希望每个人都有投票权。
因此,当习近平在国内遭遇严重反对时,我并不感到意外;但我对反对的形式感到惊讶。去年夏天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的领导层会议上,习近平显然被刹了刹威风。尽管没有发布官方公报,但有传言说这次会议不赞成废除任期限制,也不赞成习打造的个人崇拜。
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这些批评只是对习行之过甚的警告,连任两届的限制还是被解除了。此外,他还把他提炼的共产主义理论“习近平思想”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同等的地位。所以习仍然是最高领导人,可能会是终生的。当前政治内斗的最终结果仍然未知。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但开放社会还有更多的敌人,普京的俄罗斯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最坏的情况是,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学习来如何更好地压迫人民。
问题来了,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他们?
第一步是认识到危险。这就是我今晚发表演讲的原因。接下来才是困难的部分。我们中那些想要维护开放社会的人必须共同努力,结成一个有效的联盟。我们的任务不能交由政府来替我们完成。
历史表明,即使是想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也得顾及许多其他利益,把本国公民的自由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也是这些政府的一项普遍原则。
我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致力于保护人权,特别是那些没有政府保护的人。40年前,当我们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有许多政府支持,但现在已经寥寥无几。美国和欧洲曾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但现在他们已经自顾不暇。
因此,我想把重点放在我认为对开放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回答。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中国人民和习之间划清界限。既然习已经宣示了他对开放社会的敌意,中国人民将是我们希望的主要来源。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正如一些中国专家向我解释的那样,中国有儒家传统,这种传统要求当权者的谋臣在不同意当权者的行为或政令时直言不讳,即使这样做可能会遭到贬斥或惩罚。
这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中国,那些拥护开放社会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多已经退休,取而代之的是需要依靠习近平获得提拔的年轻人。但是一个新的政治精英群体已经出现,他们愿意维护儒家传统。这意味着习在国内仍将面临政治上的异议。
习把中国呈现为其他国家值得效仿的榜样,但他面临着海内外的批判。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运作多年,缺点也已显现。
一带一路旨在促进中国的利益,而非受援国的利益;它那些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主要由贷款提供融资,而非拨款,外国官员经常被贿赂来给这些项目大开方便之门。其中许多项目都被证实并不经济。
其中以斯里兰卡为典型。中国修建了符合其战略利益的港口。但港口没能吸引到足够的商业流量来偿还债务,中国从而得以占有该港口。其他地方也有几起类似事件,招致了许多国家的不满。
【译注:观察者网最近刊登美国两位教授的文章,以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为例,说明西方对中国“债务陷阱”的指控是个谎言:《狄波拉·布罗蒂格姆和任美格:掉进中国债务陷阱了?“受害者”有话说》。】

马来西亚在抵制上身先士卒。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领导的前政府(把国家利益)出卖给了中国。但在2018年5月,拉扎克被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ed)领导的联合政府赶下台。马哈蒂尔立即叫停了几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并正在与中国就马来西亚仍需支付的赔偿额度进行谈判。
巴基斯坦的情形就显得较为含糊,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投资的最大接受国。巴基斯坦军队对中国满怀感激之情,但去年8月成为总理的伊姆兰•汗(Imran Khan)的立场则更为模糊。2018年初,中国和巴基斯坦宣布了宏伟的军事合作计划。到了年底,巴基斯坦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有一件事变得清晰起来:中国打算将一带一路倡议也用于军事目的。
所有的这些挫折都迫使习近平改变了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今年9月,他宣布将避免“面子工程”,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审慎的项目。10月,《人民日报》警告说,项目应该为受援国的利益服务。
这些受援国现在得到了预警,从塞拉利昂到厄瓜多尔,数个国家正在质疑或重新就项目进行谈判。
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现在已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特朗普总统是出了名的难以预测,但美国政府这一决定是一个精心准备的计划的结果。自那以后,美国政府机构所采纳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不再让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自由发挥,而这项对华政策受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等人的监督。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在10月4日的一次重要演讲中对这项政策进行了概述。
即便如此,宣布中国为战略对手也过于简单化。中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角色。有效的对华政策不能仅是一句口号。
对华政策需要更加精密、详尽和实际;还必须包括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性回应。波廷格的计划并没有回答其最终目标到底是和中国公平竞争还是完全与中国脱钩。
习近平深谙美国的对华新政策对他的领导地位的威胁。为此,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G20会议上,与特朗普总统的私人会晤中赌了一把。与此同时,全球贸易战的危险加剧,股市从去年12月开始抛售潮。这给一直紧盯着2018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带来了麻烦。当习特会晤时,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所以不奇怪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但协议并无定论:仅仅是90天的休战。
与此同时,有明显迹象表明,中国有一场广泛的经济衰退正在酝酿之中,并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全球经济放缓是市场最不愿意看到的。
在中国,一个未曾言说的社会契约建立在稳步提高的生活水平上。如果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衰退足够严重,这种社会契约就会遭到损害,甚至商界都会反对习近平。这样的经济低迷也会敲响一带一路倡议的丧钟,因为习可能无力对诸多亏损投资继续提供资源。
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问题上,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场悄无声息的斗争。中国希望通过新平台和新技术控制发展中国家,从而制定管理数字经济的规则和程序。这是对互联网自由的威胁,也对开放社会本身造成了间接的威胁。
去年,我仍然认为中国应该更深入地融入全球治理机构,但自那以后,习近平的行为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现在的观点是,美国不应该与全世界进行贸易战,而应该把焦点放在中国身上。与其轻易放过中兴和华为,还不如对这些企业进行打压。如果这些公司开始主导5G市场,它们将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难以承受的安全风险。
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似乎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对中国做出让步并宣布胜利,同时不断攻击美国的盟友。这会有损美国遏制中国越界行为的政策目标。
最后,让我总结一下我今晚想要传达的信息。我的核心观点是,压迫性政权与IT垄断的结合赋予了这些政权监控开放社会的内在优势。控制工具是威权政权的有用工具,但对开放社会来说却是致命的威胁。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威权政权,但却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威权政权。这使得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把习近平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愿望区分开来是如此的重要。如果社会信用体系开始运作,中国人民就会处于习的绝对控制之下。既然习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特别是愿意坚持儒家传统的商界和政治精英身上。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信奉开放社会的人应该无所作为。实际情况是,我们正处于一场有可能变成热战的冷战之中。另一方面,如果习特不再掌权,这两个网络超级大国之间就会出现开展更大合作的机会。
我们仍然对类似于产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合国宪章》(United Nations Treaty)那样的机制怀有希望。这将是结束当前中美冲突周期的合适机制。它将重建国际合作并允许开放社会繁荣发展。这就是我要向大家传达的观点。
- 相关回复 上下关系8
🙂强大的对手要从内部分解入手 2 老调重弹 字562 2021-03-06 09:52:01
🙂国内社交媒体明显狗粮多了,各种攻击多了起来 白浪滔天 字48 2021-03-06 12:54:29
🙂这口才,的确很有煽动性 2 迷惑不解 字760 2021-03-05 03:22:47
🙂【原创】兵临城下(七·完)——索罗斯的宣战书

🙂索罗斯2019年1月呼吁打压中兴华为,美国同年5月把华为 CHS1 字21 2021-03-05 16:13:20
🙂2019年12月,武汉在世界军运会后发现新冠 3 ziyun2015 字43 2021-03-05 16:29:31
🙂【原创】兵临城下(六)——蓬佩奥: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 3 CHS1 字42193 2021-02-22 11:20:37
🙂【原创】兵临城下—西方对华战争的舆论准备(五):巴尔讲话 4 CHS1 字31078 2020-09-22 05: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