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原创】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系列终结篇) -- 思炎
美国佬之前吃香喝辣,志愿军伙食能比吗?
要我说,都死了才好。
都几十年了,你还没认清楚人家的手腕,不知道是谁更脑残。
有关对不回国战俘的解释:
要记得甄别和解释的不同。甄别在济州岛上的战俘营里,由美军主持,按意愿分至回国与不回国营地。解释是在停战後针对不回国的战俘,在非军事区里,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监督,让战俘本国的代表向战俘逐个解释、号召他们回国。如果他们决定回国,当场马上被本国接走。
在甄别时,亲共战俘集体拒绝叁加,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经过由美军一个个询问意愿的机会。而所谓被国民党特务控制的反共营地,倒是老老实实地一个个被主持甄别的美军询问意愿。
而在遣返解释时,阻挠解释的也是共方。
中遣会建议每天对单一围场中的共军战俘(约400-500人)进行解释,也证明一天可以解释得完,但是共方代表一直施行拖延战术,迟迟不肯进行解释。
另外,共方指示选择留下的23名美军战俘,集体拒绝出营听取美方代表解释。
由於共方解释代表的拖延,在三个月的解释期中,仅有少数共方战俘听取解释。
印度监管军控制下的战俘南营共有22,604名中朝战俘,分散在6个营区,55个围场里。围场间不相通,平均一个围场有400余名战俘。中朝解释营帐则有 32个,每个营帐里除了有数名解释人员,还有中遣会五国(印度、瑞士、瑞典、捷克、波兰)代表各一名,联军观察员一、二名,印度监管军警卫若干。
解释开始前一天,10月14日,志愿军代表要求中遣会从数个不同围场提出1000人,以备解释。10月15日,解释的第一天,491人经过解释,其中10 人选择遣返。10月16日,预定解释的1000名朝鲜战俘拒绝出营,没有解释。10月17日,提出志愿军战俘1000人,解释430人,10人遣返。10 月18日至10月30日,因朝鲜战俘拒绝听取解释,连志愿军战俘解释工作也停摆。中遣会建议先对志愿军战俘解释,也排定了人员,志愿军代表不接受。
10月31日,朝鲜战俘终于愿意接受解释,457名受解释者中21名遣返。
11月1日,中朝方又出状况,要求对解释营帐及解释区250个候讯场所中的战俘广播,并且于同时进行解释。印度监管军认为这种同时并进方式会造成骚动,无从应付,建议只在候讯场所广播,并于广播后再进行解释。中朝方不同意,当天解释停摆。
11月2日,经过再三折冲,中朝方终于接受印度监管军对广播的建议,但当天已无时间解释。
11月3日,首次对单一围场进行解释。一个围场中的483名战俘完全完成解释,19名选择遣返。
11月4日,拖延战术开始。单一围场的403名志愿军战俘,仅有205名经过解释,2名遣返。11月5日,单一围场中的408名志愿军战俘,136名完成解释,2名遣返。除遣返战俘外,其余根据事先与印度监管军的协议,全部都回到原来围场。11月6日,中朝方抗议已经解释及未完成解释战俘没有隔离,要求对未完成部分进行解释。这些战俘拒绝出营继续听取冗长解释。中朝方坚持要隔离,也不愿对其它围场进行解释。解释工作停顿至11月15日。
11月16日,对G53围场407名朝鲜战俘提出解释,只有227名经过解释,6名遣返。中朝又拿隔离问题做文章,解释工作停顿至12月20日。
最后解释工作,从12月21日至23日,有781名志愿军战俘完成解释,其中69名选择遣返。
不可讳言的,在这些战俘中,确有反共战俘领导的组织存在,就跟当初甄别时也有亲共战俘领导的组织存在,双方进行激烈斗争一样。但这些人毕竟是战俘,未来不确定,对于联军方面会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出卖他们也在担忧。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会有较激烈的动作。但要说什么台湾派遣的特务混入,还能派几百名“特务”冒充战俘听取解释?那是笑话了。
要说反共战俘的头头能够安排强烈反共的人先上场,来个下马威,那也是志愿军代表自己制造的机会。从不同的围场提人,自然有可乘之机。只要改为对单一整个围场解释完,再换下一个围场,就没有这种问题。不是说不遣返战俘的大多数都是被裹胁的吗?那一个围场一个围场地解释,哪还能有这样示威的机会?更没有谁被解释,谁不被解释的问题。志愿军代表又不是三岁小孩,连这点都想不到吗?
而且,一个围场只有400余人,从头两天的经验知道,一天应该解释得完没有问题。更何况头两天要求遣返的20人,绝大多数都是一进营帐就马上表示要遣返回国,根本不花什么时间。如果被裹胁的多,那一进解释营帐,有机会表达意愿,自然也不需要太多时间解释。不是吗?
中遣会的瑞士、瑞典代表撰写的“委员会少数报告”(当然,捷克、波兰都不愿意具名)中,对拖延的原因有如下说明:
“从事解释的一方,一再变更其进行解释工作的方法,有时使委员会不可能在接获通知后的短时间内,允从其所提新而不同的解释方式的请求,或使监管军难于劝服战俘出面听取解释,或致使战俘拒绝出席其后的解释。
在这方面尤为重要者,即在南营(按,对志愿军、人民军战俘解释区)中从事解释的一方,自从11月4日以后,对进行解释工作的拖延,在此种拖延的方法下,个别的解释延长达五小时之久,此为战俘们所认为是加诸他们的不当的压迫,解释工作乃不能向每一日内所有被要求出席听取解释的全体战俘进行。如果南营中从事解释的一方曾采纳委员会的建议,此即系以每一场合中可行性为依据,例如在朝籍战俘不愿出席听取解释时,即行向愿意出席之华籍战俘从事解释,并按日向一个围场 ──或数个围场──继续进行解释,则解释工作在10月15日以后已可每日依次进行。甚至在该日期以前,解释亦已可在该时所有的设备中,于有限度的规模下进行。”
按,最后提到10月15日前的解释,来由是中朝方挑剔联军建设的南营,在9月28日要求换地重建,联军认为出尔反尔,而且中朝建议的施工地点可能布雷,不愿意重建。后来证明该地施工困难,中朝又提出另一地点,中遣会在10月2日说服联军重建。联军10月3日答覆,建议先花一个星期建一个有20个营帐的临时解释区,先开始解释,后面再补建其它设施。最后在中遣会协商下,连日赶工,在10月13日全部完成。联军方面对北营只要求修改,未要求重建。

这张照片可能要比任何字眼上的争论都有用。
解释营帐里的布置与解释的进行,可能是对朝鲜战俘的解释。战俘逐一接受解释,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五国代表在旁监督,印度士兵监视战俘。其它战俘要如何能控制影响正接受解释的战俘的抉择?难道是念力?
如果战俘中大部分都想回国,为什麽不让他们有走进这32个解释营帐之一的机会?为什麽不一天一个围场完成400馀人的解释?为什麽共方解释代表要使用拖延战术?
哈哈,你说你不看那种马路货的报纸,请问你贴中文字的来源?
还
笑话!我这里也给你照片看看!
首先,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您还没有给大家:美国没有动用细菌战的论证呢!请返回完成
关于志愿军战俘的接收工作,中国方面从战争初期就已经开始与美国方面进行接触了。援引美援朝时期担任志愿军第六十五军一九三师政委的贺明的回忆:1951年12月,朝鲜战场停战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遣返战俘问题。中方谈判代表团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即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中“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规定的办。
但美方代表却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载:如果把包括投降在内的战俘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无人逃亡。他还认为,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的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由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立场不同,谈判漫长而艰难。在双方提供战俘资料时,美国方面在战俘数字做了四次变动,最多时11.6万人,最少时7万人(含朝鲜人民军)。从1951年12月1日谈判进入第四议程——关于战俘遣返问题,到1952年11月,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战俘问题因此成了停战谈判的难点。
第四议程后,双方又经过一年半多的谈谈打打,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签定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在本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各方面应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决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各方应将未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此项规定,中美双方将采取自愿原则让志愿军战俘自行决定去向问题——战俘们可以自由选择回大陆或去台湾,而这项工作由中立国——印度来主持,以确保任何一方不得采取胁迫手段,所有战俘的选择确实是出于自愿的。
1953年9月9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的蒂迈雅中将为主席,捷克斯洛伐克的衔西莫维茨上校、波兰的衔加耶夫斯基、瑞典的斯坦斯特鲁、瑞士的邓尼克为委员。
按照规定,在印度代表主持的解释营帐中,战俘们将按照顺序进入解释营,分别聆听中共代表与美军代表的解释,最后战俘们做出决定,回大陆的由中共代表的这边出口出去,去台湾的则由美军代表这头出去。
但关于“解释”的过程显然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此前后,美国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小动作。据《文史博览》(2005年第9期)记载,到了1953年9月6日,双方直接遣返战俘“交换完毕”,但是,美军手上尚有14235名志愿军战俘未被遣返,美方称这些战俘自己拒绝返回共产主义阵营。当时,板门店附近的军事分界线南北两边都设立了“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在分界线以北的“北营”尚有359名联合国军战俘;分界线以南的“南营”有22604名中朝军队战俘,其中中国战俘14704人,多出了四百余人。
9月21日,朝鲜和中国方面提交美方一份98742人的朝中被俘人员名单,要求对方交待这些人员的下落,但美方一拖再拖,经再三催促,直至1954年5月13日美方才交待,其中27000人在停战前“逃亡”,22000余人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37900余人已作为平民处理。朝中方面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诚实的交代。此后,一直没有下文。
根据规定,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解释工作应在9月25日开始,但由于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营场,致使解释工作推迟到10月15日才开始。朝中方面坚决要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隔离战俘解散特务组织,将经过解释的战俘与未经过解释的战俘隔离看管。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以解散特务组织有困难,“战俘代表”拒绝隔离等理由,拒绝了朝中方面的要求。
据《战俘营纪实》记载,朝中方面的解释代表利用广播,播送《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朝中解释代表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讲话》,打消被俘人员的顾虑,使他们知道有行使遣返的权利。但这项解释工作所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其中当然有美国方面的阻挠甚至恐吓,但也不乏有些志愿军战俘鉴于当时的形式希望投靠台湾方面。
而美国方面直到12月2日才开始进行解释工作。战俘们平静地听取美方的解释,没有任何暴力的表现。但美方不肯给予战俘更多的解释,拒绝回答战俘提出的有关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的问题,并对战俘进行侮辱和威胁。
12月11日,战俘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美方改变态度前拒绝走出营场。美方不能为战俘的和平生活提供保证,因而,经过解释后,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期间,仅有10名战俘改变决定要求遣返,2名南朝鲜战俘希望到中立国,绝大部分战俘拒绝遣返。于是,美方解释工作遂于12月12日起停止。
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不顾朝中方面的反对,于1月22日午夜撤出印度部队,放弃对北营战俘的看管,致使北营战俘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次日,中立国遣返委终止了对战俘的看管,并很快解散。
1954年1月20日,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南营重新移交给联合国军看管,由联合国军负责把这一万多名志愿军战俘运送往台湾。当年任职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厅长赖名汤负责该次行动。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终止看管工作后的1954年1月23日,1.4万多名志愿军战俘全部换上国民党军装,于凌晨3时许分乘225辆美军大卡车,离开中立区印度村。上午8时起由韩国仁川港搭上16艘美国军舰,浩浩荡荡地驶向基隆。惟一显示与台湾相关的是台湾出动海军5艘中字号登陆舰。
为了迎接这一刻,国民党动员了许多欢迎群众,开启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并将1月23日这天定为“自由日”。能成功策动1.4万多志愿军战俘来到台湾,对当时的台湾蒋介石政权的确是一件大“喜事”。志愿军战俘交由蒋经国领导下的一个辅导组织负责,逐个审查后,补入“国军”基层监视使用。
至于为何会有这么多的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的问题,后人有诸多解释。但对于那七千多名返回大陆的志愿军当时的状况,大陆方面的各项记载都对美国多有指责,称这些志愿军被俘人员,不仅个个精神上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而且大多数人的肉体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6000名被遣返的志愿军被俘人员中,有1609人是严重的病、伤、残者。在1172名外科病历中,有840人或说71%的人被截肢而致残。在261个被截肢者中,共截下来360截肢体(上、下肢),那就是说,有半数人被截下两截肢体。最为残酷令人不忍睹的是,这1172人中,竟有十多人是只剩下躯体没有四肢的全残人,其中多人原来不过只有一点冻伤而已。”


还有,被逼去台湾的赵英魁的口述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
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还有些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
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反共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连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故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
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牢狱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军与国民党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
船抵达台湾基隆,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
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经历。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快要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
1,文晓村,此人后来成为有名的诗人.
再过几个月之後,有一个军官,来到我们的房间,给我们每人发了四套黄卡基军服,四条黄色军毯,说要送我们回国(Go home)。我们抱著希望,在宪兵押送下,送上一架军用飞机。下机之後,接机的是几位穿着军服的国军军官。他们说:
|「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欢迎你们回到自 由祖国的怀抱。」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
四十六年後的今天,当我执笔写到这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不是我们的自 由意志,这不是我们的自 由选择。至少在那个时候,这是事实的说明。
但这却是美国式的「尊重人 权」!美国式的「自 由选择」!多么具有讽刺的意义。
2,马金盈,这可是一位自愿赴台的战俘,
在濟州島的後半段時間,就有消息聯軍與共軍談判的情況,將來可能要交換戰俘,對於戰俘營的領導們,以及中華民國政府,都相當的驚覺,紛紛提出對策,不斷加強反共標語的刺字,造成戰俘們的心理恐懼。
3,冉宏图,这是一位在凤凰卫视上作过证的老兵
......
冉宏图:从韩国到台湾运走的时候有的偷着就跳船、跳海了。他说‘我去到台湾也是死,我回到大陆也是死,我干脆死到海里算了’;他说‘我知道,我也了解部队的情形,没有办法交待,死路一条,今天刺了一身字回到大陆去也是死,那我干脆去到台湾,去了台湾想法不一样、变了的话,我还是死了算了’。我说‘你不要那样想,不是个办法,我们活一天看一天,究竟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形’。不听劝,你怎么拉得着,他头一低就跳海了。
......
冉宏图:在台湾烧纸,晚上做梦都想到想到母亲,想到弟弟,现在还在想我爷爷、我奶奶他们,也想邻居、我的家婆。我现在回想那个面容,现在看都一样;听到哭的声音,上气接不到下气。见到我婆婆的面容就是不讲话,那是个梦。那个时候我们说回不来大陆,干脆死了算了,来了台湾还受了很多折磨。往床上一躺,那个脚就把扳机扳着,枪抵着胸口。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我都没有自杀,只能够晚上掉眼泪。我说我还要活下来,回来看一下,对家里有一个交待,活不下来就算了。
LIGHT先生,这些资料不是共党的宣传吧,面对这些资料还要鼓吹"战俘赴台是自愿,遭迫害是共党宣传",那些无耻的东西是谁?
是你,和战史沙龙那帮畜生.![]()
![]()
![]()
土共的宣传过去是,现在还是比美国的宣传差了几个级别。比起轮子,海外自由民主运动人士和西方媒体睁眼说瞎话来,土共僵化的宣传还要靠谱得多。同学,今年是2010年,如果不知道“洗脑”这个词咋来的,还是去查一下,真是很有喜感啊。
我已经说过了,像文忠志的书和半岛电视台的影片这种阴谋论的东西,都是以少数的史实,用极大的想像来膨胀,缀以牵强附会的文件,使用跳跃式的论证手法来推演出一堆虚幻的东西。
翻翻旧文,几年前为了消遣自娱,也写过类似的东西,现在就贴在这里,让大家叁考比较一下。
拙作的方法跟文忠志的书以及半岛电视台影片的手法如出一辙,引用部分史实(长岛号作战资料,Area 51资料,二战战史),用想像力无限地膨胀,运用巧合之处,跳跃式牵强附会地论证,建立了一个表面严肃内里搞笑的说法。要不是最後贴那张照片,读者恐怕都半信半疑了。
河众许多都是知识份子,看了後自能分辨黑白。少数梗着脖子睁眼说瞎话的,自便吧。
思炎对几十年的喉舌宣传情有独锺,老是抄这种重复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编剧,真不晓得是为了什麽。
就如这里说什麽美军选择不遣返战俘听取美军解释,根本是狗屁。当时志愿军俘管怕这23名美军改变主意,在他们里面搞小组织、搞集体行动,不让他们去一个个地听取解释,还要他们绑架印度军官进行斗争,跟张泽石等亲共战俘在战俘营里搞的那套如出一辙。
像你上面说的什麽美军战俘听取解释云云,只能骗自己人民,骗不了外人。像这里这个俘管的也在睁眼说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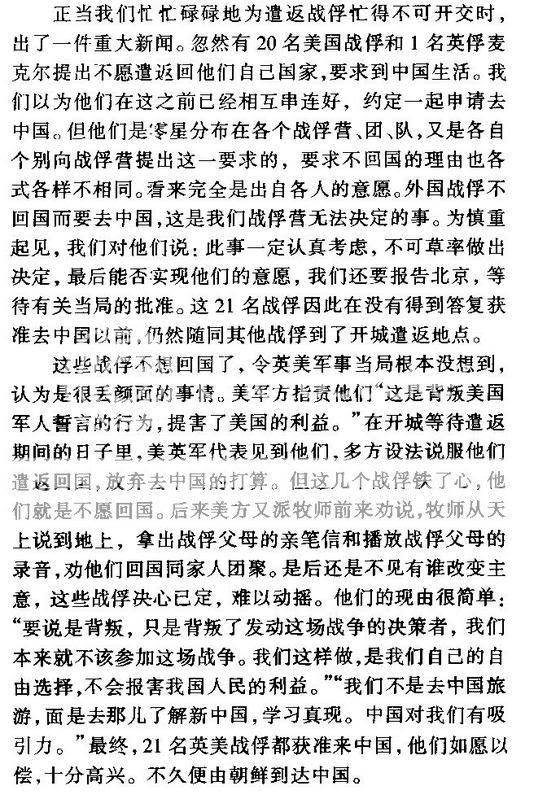
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23名美军战俘集体行动,但其中两个人还翻墙逃跑,让志愿军俘管更不放心,透过潜伏在解释区中遣会医院里的俘管领导指示,根本没让他们去解释营帐逐一听取解释。这里是後来留下来的21名战俘之一的回忆录,自己看:
Morris R. Wills: Turncoat, An American's 12 Years in Communist China, Prentice-Hi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6
投奔(Defection)
1953年8月6日,战俘营的指导员叫我过去,说我下午要调到5号营;这时5号营的战俘已经遣返完毕,我们看到他们坐卡车路过我们营地。指导员甚至不让我回去拿东西,他把我的行李带了过来,怕有人对我不利或者攻击我。这时已经是最後阶段,营里有些人已经表明态度不想回国,(营里)一般都认为他们是叛逃。
我想你可以叫我投奔者(defector)或改换阵营者(turncoat),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变节者(deserter)或叛徒(traitor),因为美国和中国人签署过协议,如果想要的话,我有权利到中国去。根据这个,我就不是叛徒。再说,我的待遇也不好,我们被扔在这里,被外界完全遗忘。他们显然没有尽力要让我们重获自由,他们遗弃我们,把我们留在这里整整两年,自己却在国内过好日子。
那时候,经过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训练后,我心目中并不认为自己在叛逃。我认为自己仍是美国人,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以另一种方式来帮助美国,也许以后我能帮助改变体制,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当然,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一点也不。
1号营中我们连里只有另外一人也来到中国──和我同一天被俘的上等兵Richard R. Tenneson。即使是他,也是直到在营司令部见面时才知道我要去中国。还有其他更多人本来应该也要去中国,但是中国人行事非常隐秘,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谁要去中国。我们连里应该还有另外4到5个人,而1号营5个连中应该可能有多至25人要去。
我必须和连指导员面谈,他想确认我不会改变主意。他说我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国没有美国那样多的物质条件,我必须准备过着物质条件较少的生活。我告诉他说我知道中国很穷,生活条件没有美国那么好,但这对我的决定没有任何影响。
接着我们被带往营司令部,之后Tenneson和其他连的许多人也陆陆续续过来。他们把Tenneson、我及另外三个人送上一辆敞蓬俄国卡车。日後那三个人被中国人刷下来。Tenneson和我一样也经历了转变的过程,但他在战俘营中非常敢言,给他招惹了很多麻烦,有一两次其他人试图在晚上修理他。我以前一直避免被人看到和他在一起。
吃完午饭后我们离开1号营,卡车上没有卫兵,只有前面开车的中国司机。现在是我们第一次获得信任——完全的信任。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在鸭绿江南岸的5号营。你可以看到对岸的中国。一些中国指导员在等我们,这是他们第一次称我们“同志”。
我们见到了从3,4,5号营过来决定留下的人,他们互相称“同志”(2号营是军官营)。我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来决定哪些人我喜欢,哪些人不喜欢。有三四个我根本懒得搭理──都是喜欢自吹自擂之辈,我拿定主意要跟另外一些人保持距离。这里总共有27人:21个美国人后来去了中国,另一个苏格兰人Andrew Condron,原来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以及五个后来没去成的。
两个中国人担任我们的教官,一个姓田,资深红军政委,一个秃头老头戴一副眼镜,至少六十多了。另一个姓张,是他的下属。他们和优异的翻译一起过来,马上把我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紧密的群组,进行有系统地训练。当时我并没有觉查到,但是现在回顾的话,这是一道程序让他们来判定哪些人能坚持挺过停战协定中规定在中立区停留的三个月。他们要尽力找出我们中间是否有人是被送进来搞破坏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中国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都要剖析自己,并被其他人所剖析以决定他是否合格能不遣返,是否能挺过三个月的时间、保持对组织的忠诚?
我们开始按照被教授的方式来开批评会。每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解释他为什么要去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被遣返,那些在战俘营里的旧识必须要提出对他的看法。每次两个中国教官都在场,来确认每个人是否诚实。我们也选了组长,上士 Claude Batchelor和军士 Richard G. Corden被选为正副组长。
后来,那三个月解释期过了之后,这两个中国教官告诉我们当时对每个人的评价。我被认为是一个相当保守、平静的人,应该可以挺过这三个月,不会替组织惹麻烦,也不会改变主意。他们把我的成分划成“富农”,因为从我的自传中得知,我父亲有175英亩土地。这在美国不算什么,但对中国人来说这相当于超过一千亩土地——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因为我父亲没有雇工,他没有被划为地主,他被认为是“富农”。因为我是他儿子,所以我自然也是划为同一种成分。每个人都必须被划进某种成分里。
然而,习惯上,中国人总要拿些人树立榜样。他们发现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从1号营中来的,曾经和朝鲜人做过大麻买卖。中国人在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田教官宣读了对这三个人的指控。到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感觉自己非常的“进步”,认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每个人都是同志,也应该表现的像个“同志”那样。中国人暗示这三人都是被派过来搞破坏的,鼓励其他人起来对这三人进行批判。他们一步一步的上纲上线直到那三个中有人眼泪都下来了——开始啜泣起来。最后,正如中国人期望的那样,这三人改变了主意,“自愿”要求被遣返。中国人为他们开了一个欢送会,对他们说他们还是“和平战士”,并且希望他们回到美国后继续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作斗争。
在5号营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是社会主义圈子中的一员,和这个组织中的其他人关系密切。我认为我应该尽我所能对这个组织中的所有人在意识形态上提供帮助。我认为自己是个和平斗士,想尽我所能在这个世界上争取和平。我觉得社会主义,以及最终的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些强烈的感觉源于我在1 号营的学习经历。虽然我当时并不觉得,但你可能要说我当时是被洗脑了。
在5号营我们被教导要维持组织的团结,要有对组织领导的责任感。中国人让我们相信这是一场我们必须面对的斗争,只有“英雄”、佼佼者,才能挺过中立区的解释阶段。
我们在中立区的三个月将受印度军队管辖。我们将完全靠自己;理论上不会和中国人有任何联系。美国陆军的“解释人员”理论上应该有机会对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回国。因此,我们在五号营进行了模拟训练对付这些解释人员。我们被命令在面对解释人员时要制造麻烦,让他们解释不下去。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唱歌,制造噪音,把背转过去──任何可以不听取解释的事情。我们应该攻击美国的外交政策,指责美国是战争贩子。
这时我还不知道,但中国人在我们组织里又设立了另一个组织,在这个核心组织中有 Batcherlor,Corden,Sullivan。他们和这核心组织安排了一套灯光密码,以便与在中立区的我们直接联络。灯光信号在夜间用过几次。他们也试图训练我们的吉祥物,叫Nonrept的小杂种犬,来传递信息,但没有成功。张教官还计划把头剃光、混进营里的医院里面做苦力。我本来不知道这事,但三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我去医院补牙,发现他在那里,他叫我别声张出去。
在我们前往中立区的前夕,中国人为我们办了一个酒菜丰沛的盛大宴会。我们开怀畅饮,中国人也一样,有一些人不得不被抬着回去;有个家伙甚至他自己的床烧掉了。像这样的活动一是为了把我们团结起来、巩固组织,二是为了让我们的情绪充分发泄。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送上卡车,开了两天才到中立区附近的开城,沿途土路又窄又崎岖,我身体还从来没有这么酸痛过。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营区里一个星期,并且被安排到一个显然以前是富人专用的漂亮朝鲜澡堂洗澡。我们又开了很多次会,准备如何应付解释人员。如果有人表现落伍的话——例如对性感兴趣——他就会被别人告发。所有事情在中国都是以这种方式极有效地掌控,你总是隶属於某个组织的一部份,假如这个组织有二十个人,其他十九个就会持续监视你,你也要持续监视其他人。任何事都必须汇报,否则的话你将被人告发你不汇报,你不得不照着做。这就是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四分五裂的原因,也是人民为何还没有起来反抗的原因。
在中立区我们被安置在一处特别营区内,在一个小山上,大约两英亩见方,周围被铁丝网环绕。这是我们被俘后第一次住在铁丝网里。远远望到这个营区我们就开始唱歌,印度人就在那里,还可以看见一些美国军官。我记得那里有一些美国司机聚在一起,当我们唱“国际歌”的时候他们也开始唱美国国歌,他们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了,因为不记得歌词,我们这边就大笑、喝倒彩。
我们被安排到营房里安顿下来。慢慢地,组织里的成员一个接着一个地到铁丝网围绕着的医院去,并且呆在那里不回来,最后只有八到九个人留在营房里。当时我还不知道张教官就在医院里,并且直接控制着那里的人。解释期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组织内部的那个核心组织。我并不介意有个核心组织,但是却不太高兴自己不知情,我对有些人更受信任感到反感。这造成意见不合,我们的组织现在开始有裂痕了。
组织里有两个人最後决定还是回国。一个是Edward S. Dickenson 上士,他就睡我旁边,晚上的时候常常弹吉他,我们一起坐着唱歌。他假装头痛乘隙溜走了。另一个是Batchelor,中国人认为他是5号营里最“进步”的人,在他们的指引下,Batchelor被选上担任组长。他人非常好,非常真诚,但就在待在中立区快结束的时候,他收到了日本妻子的一封信,当天午夜他就走了。
我确曾几次思考过自己的决定,但是我很固执,我在战俘营就已经拿定主意,不会轻易改变。我决定不让这件事情困扰,不要再多想了。
我们一直对印度人找麻烦,抗议他们的牙医试图影响我们,抗议给我们送来圣经。中国人也命令我们绑架营区的印度指挥官,以迫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派人过来听取我们的抗议。我们对此争议很大,我是几个反对的人之一,我认为这相当愚蠢。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来自中国人的命令。最后,Batchelor取得了大多数的支持,我也不得不同意一起行动。
组里一些人把那个军官骗到我们的营房中,不让他出来。当我们抓到他後,印度人就在营房外围架设机枪,并且开了一辆坦克过来。中立国委员会几个小时之后才有人过来,最后我们呈递了请愿书之后把那印度人放了。
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去见解释人员,由於中国人的阻挠,整个解释程序无法进行。在我们到中立区大约两个月以后,我们被转运到另一个营区,非常小,因为形状就像香蕉,我们叫它香蕉营。至少有一天,美国人开车载过来一个扩音器,宣布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他们没有威胁我们,只是给我们了一个最后期限——我记得大约是五分钟。
我们已经对这种事情有了准备,我们都不去听广播,因为,一旦你开始听,你就会开始想,你就开始动摇起来想回国了。对我而言,这样做不仅仅是违背我对我组织的诺言,也是背弃我自己的决定,即背弃我自己。
那些美国人等了大概五分钟,看到没人出来,他们就拿下扩音器离开了。
这时我们组织里已经有了很严重的意见冲突,我们已经厌倦了集体生活,而那时我们也没有和早先一样地被严格控制。当Batchelor走的时候,我们组织就分裂了。简直不可想象一个组的组长会走,他从来都是最受信任的,并且一直努力保持组织的团结。我们对他更觉得难过而不是愤怒,每个人都喜欢他。我们认为他会入狱,实际上也是如此。
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营门洞开,并且见不到一个人。印度士兵已经走了,中国人过来接管,张教官也从医院过来。我们又在营里面住了几天,接受两个亲共记者 Alan Winnington和 Wilfred Burchett的采访。中国人同意在平壤举行一场公开记者招待会,我们又花了几天的时间来训练——可能会问什么问题,以及怎么回答。我们要强调麦卡锡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和平。Corden现在是组长,他已经二十五岁了,从1946年就就在美国陆军当兵,也是我们这群人中智商最高的。他发表了一通演讲,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回答了问题,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我们预期的那些。
之后,我们就准备去中国了——二十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海军陆战队。组织中的一些人想去苏联而不是中国,但中国人和他们个别谈话,说服他们都去中国。接着田教官宣读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接受我们作为自由的美国公民到中国去。又开了一个宴会,我们和中国人都喝醉了。
我们在开城呆了几天时间,订做平民服饰,在城里面转转并且四处观光。他们为我们弄了一列特别列车——车头,两节车厢,以及两节装载我们的俄国吉普的平板车。我们穿过朝鲜,看到了平壤的废墟,没有一栋房子还立着,人们都生活在山洞里。中国摄影师上车为我们拍照。1954年2月24日早晨大约4点钟的时候我们跨过了鸭绿江到中国境内。我从窗户望出去,外面雾蒙蒙的又冷——非常黑,非常灰暗,非常冷。
从你贴出来的东西里,就可以看出中方比美方人道千万倍!
我们已经对这种事情有了准备,我们都不去听广播,因为,一旦你开始听,你就会开始想,你就开始动摇起来想回国了。对我而言,这样做不仅仅是违背我对我组织的诺言,也是背弃我自己的决定,即背弃我自己。
那些美国人等了大概五分钟,看到没人出来,他们就拿下扩音器离开了。
即便是你特意标出的这段,也说明了,即便当时没有去见解释人员,但他们可比志愿军俘虏幸运上万陪。美方喊话后,是美俘自己不回去,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而志愿军被毒打,刺字,被逼去到台湾的呢???如果您有人性的话,为何对美国这种无耻作为闭上眼睛?
[FLY]大家都等着你的美国没有动用细菌战论证呢[/FLY]
此文由LIGHT先生发表:
此文由赴台战俘文晓村(后为著名诗人)在其自传中的回忆:
再过几个月之後,有一个军官,来到我们的房间,给我们每人发了四套黄卡基军服,四条黄色军毯,说要送我们回国(Go home)。我们抱著希望,在宪兵押送下,送上一架军用飞机。下机之後,接机的是几位穿着军服的国军军官。他们说:
|「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欢迎你们回到自 由祖国的怀抱。」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
四十六年後的今天,当我执笔写到这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不是我们的自 由意志,这不是我们的自 由选择。至少在那个时候,这是事实的说明。
但这却是美国式的「尊重人 权」!美国式的「自 由选择」!多么具有讽刺的意义。
呵呵,战沙出来的,别的不行,心理素质都是很高的嘛.
830名英俘仅死十余人,209名土耳其俘虏无人死亡,三千美国俘虏死了一千多人...
中国存心只虐死美国人,对英国人和土耳其另眼看待是不是?
八百多英国战俘死了十来个,209名土耳其战俘无人死亡.
>>>来,咱看看老美,老英,老土各自的疗效如何.
您在说自己?
当年的战俘现在还有活着的啊,他们的证言不算数么?当年去台湾的战俘也有同样的证言啊。如果GCD能够让他们如今作出有利于GCD的证言,当年又怎么能让他们去台湾呢?
战沙的老大们,你们要点脸,非得把细菌战的问题转进到战俘问题么?做人别那么无耻。
要是都死在朝鲜人手里,的确是死的越多越好。
可惜tg不是金日成的棒子党,根本不在乎什么声誉。
tg恰恰就是很想在洋人那里得到个优待战俘的声誉的。后来又搞运动会,又请外国大鼻子记者采访不就是为了这个嘛?
死了的都是该死的。
你这美国崽还真爱面子啊,什么事都往面子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