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有关元清非中国的说法,补点明朝的看法,这个观点早就有了 -- 阴霾信仰
陆军横扫大漠,海军横行东太平洋,东南亚,印度洋,东非, 是世界第一个陆海兼有的大国. 新中国很牛逼,但到现在都还未达到那时的高度吧.今不如昔,这有什么不好承认的.你是不是要吐血啊?
换到今天肯定吊打解放军,拳打美利坚,脚踢俄罗斯,核平小日本,陆沉英吉利,一统地球,指日可待。
明教教主,您当之无愧。
义和团才是反帝反封建。
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天国时期,资本主义还没有进入到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记得老师提醒过,这个是易错的考点。
还是我记错了?🤔
清朝末年,农民起义又开始活跃,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一般认定为“反帝反封建”。
更严谨的提法是:反封建反侵略。
反封建是在反侵略前边。
这一时期,侵略者的提法是“西方殖民者”。
和西方人有共同信仰,可能比较亲近。所以派人联系,希望这些西方人能帮助自己推翻满清。但是太平天国绝对是不允许租界和特权的,这些侵略者很不满。开始确实有少量西方人帮助,但是很快,西方政府就协调了立场,传教和利益比起来,那算什么。很快侵略者就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了。这个有点类似少量美国人斯诺,史沫莱特等同情支持共产党,但美国政府是绝对支持蒋介石的。
我们的文化出了大毛病,心里想的天下,可是没有征服天下的武力,心里想着的天下只能是痴心妄想。在这种痴心妄想的文化加持下,能是什么结果?
问题在于经验结构没有变化。或者说沿用的经验和事件实际上都是经过限定的理论化经验,而不是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生搬硬套。
(以上出自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
龙眼兄的说法其实就是「水舟无关论」,直到现代还能看到类似的观点,并且拿抗日或者内战时期大部分生活区相对平稳作为例证。不讨论后来的三光,理论上生活平稳的确可以得到充分实证,只要不涉及价值层面的秩序的话。
但是历代农民战争、中共胜利的法宝,难道不会让这个预设失效吗?不在乎王朝统治者的阶级,恰恰是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后的产物。也就是宋明以后的地主阶级,由于政权结构的改变,自治权力的增加,作为地区行政的主导力量,已经「皇权不下县」了。他们自然可以不在乎中央如何。可是之前社会,不管是贵族、门阀,中央、地区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在当时的政经社会背景之下,是不可能不在意的。就算你自证无意政治,人家也不信。如果自己有力量保护,族群也不可能不要求你谋求更多。
然后,不在乎谁来当皇帝,恰好只有在换代的时候出现,因为新兴政治实体的力量不足,需要和地方权力妥协,才能完成统治。也就是说,反而是换代让这种不在乎谁来当皇帝成立,只要脱离这个背景,比如力量强大、区域自治,这种现象根本无法成立。
这还是不讨论本位主义、阶级利益还有古代天下观的崩溃。唐宋西域知识的冲击,明清西方势力的入侵,看看明朝的万国舆图是什么样的,一般人的认识是什么样的?
结果就是,龙眼兄的的预设无法成立,那就是所谓「古人的眼光看」和「谁来当皇帝」并没有直接的线性关系。反而会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说法。虽然这是明遗老的说法,但作为一种理论,先秦已经完成。也就是之前说的文明——人心秩序。政治秩序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问题反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管控,使得这种思想被蒙蔽。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实际上那些出卖国家换取保障的集团,最后都没好下场。也许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族群,维持了族群对地域权力的长久,可已经不再有之前的权力地位了。乌衣巷不姓王。当然,愿意当奴才的除外。
因此,我觉得龙眼兄的论证称不上合理,尽管大部分表述是对的,对最后一段也基本认可。但总的来说,不像胡辣汤兄说的那样,出了大毛病。
要知道,绝大多数人其实没有天下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所谓天下,是指人心的天下——是指承载人类社会的疆域,是指照亮这个疆域的人心。
不是地理。勉强可以说是某种「普世」的思维。在这种思想主导之下,现有的所有政治实体,都只是「武霸任力」而已。只是国家,不是天下。
作 者|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
余英时先生曾感叹明代王阳明这样的大儒都有被扒下裤子打板子的经历,与宋代王安石和宋神宗勾肩搭背地共治天下的美事简直没法比。可是再看看清朝,你就会觉得官员被公开脱裤子打板子已是一种幸福,这就是我读清史倍感郁闷的一个理由。
近翻《鲁迅全集》,猛然发现鲁迅先生已提前感受了类似的郁闷。鲁迅当年讲了一个文字狱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山西汾县的傻帽书生叫冯起炎,等皇上出巡时拦驾,呈上自己的经书,非嚷嚷着要让乾隆爷披阅,如此犯混也就罢了,他随文还有段话却更离谱,说是自己看中了亲戚家的两个漂亮姑娘,这家伙在泡妞方面有点底气不足,怕人家瞧不上眼,却又贪婪得两个都想要,心想这回可找到皇爷给撑腰了,于是很自信地说,如果乾隆爷您差个干员,派个快马和地方官知会一声,两个妞奉旨后照单全收,这事不就全齐了吗?那话透着股肉麻的亲近劲儿,好像乾隆爷就是他老爸。
按鲁迅的话说,这傻帽儿不过是中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毒,总想着天子做媒、表妹入怀的大梦。傻是傻到家了,可人家的初衷不坏,起码是视皇如父,对自己老爸撒撒娇总是可以的吧,这在前朝有的是先例,明代的皇上恐怕还巴不得臣子如此献媚呢。可这次娇却撒错了地方,这才子的结局是被他的皇帝老子发配出关去了。
因此,我以为,清朝比前代更恶劣的地方在于,前代下人想做奴才,主子会假装高兴,至少不至于屁股被板子打烂,到了清代,做奴才还得排队等候,看主子的眼色,随便夹塞插队的后果就是挨揍,弄不好还得被发配到蚊子成窝的地方去。
骂人当然要杀头,吹捧也得看场合,这“思不出其位”的火候实在是太难把握了!想要修炼到家非闹成心理变态不可。还是鲁迅看得清楚,他说,如果您对乾隆爷说这龙袍旧了,咱还是补补吧!进言者以为是尽忠,在皇上眼里却是大罪!那补袍子的话轮得着你说吗?轻则流放,重则砍头!
没错,和明代比,清代获得了大一统的地盘,也拥有维系这个局面的超级能量,正因此,清代皇家为维系这个放出的大烟花不破灭,终使清朝变成一个千方百计让人活得难受的朝代。难受到什么程度?不是一般的打杀和廷杖,而是用无穷尽的洗脑暗示杖杀你的心灵,过程犹如慢工出细活般小火煎熬,最后过滤出的,是一个个精神药渣。
乾隆这个心理大师有话不明说,让你自己琢磨,等你琢磨错了,他便突然冒出来扇你一个嘴巴,你甚至来不及揉揉痛处又得巴巴地继续琢磨,直到嘴巴抽多了,脸颊红肿起来才知道那线该踩在哪里。这番操练的化境就是嘴巴不用皇帝来抽,自己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抽自己,或是该抽哪个部位,作践脸颊的习惯一旦养成,就会发展到每天不抽嘴巴就不舒服甚至活不下去的地步。
自己抽嘴巴的例子,也发生在文字狱密集的乾隆时代。《四库全书》的编修进度和诛心文网的编织几乎同步已不是什么秘密,《四库》书收得全,毁得更狠。可最初,这同步奏鸣曲只是乾隆爷一人谱出来的,如何变成官员士人的混声合唱还得费些心思。
据说当初查书的阻力就来自地方官,因为他们实在不知什么应该算作禁书,常常草草交上几部搜出来的书就想蒙混过关,此时,乾隆爷的巴掌会呼呼生风地扇将过去,奴才们脸上泛出了红手印,缴上来的书也变得越来越多。其实禁书的数目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嗅觉的培养和态度的规训。
聪明的人脑筋转得就是快,几个巴掌扇过去,一个叫海成的江西巡抚出主意说,光注意大地方还不够,说不定那些文盲白丁的家里还藏着违碍书籍,也许是个搜查盲点。乾隆爷心里暗喜,这奴才开始会扇自己嘴巴了,免不了大大奖赏一番,其他人一眼看明白了,赶紧跟上,于是蜂拥而上出了更多更馊的主意。
有人说,应该派些闲散人员挨家挨户地搜,大有挖地三尺的意思,乾隆爷虽觉这办法有些过于阴损,可还是忍不住高兴。让乾隆爷有些尴尬的是,靠扇自己耳光换取表扬的海成那厮却得好卖乖,某日想出了一个世界上最馊的主意,他说,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在写完书后应一律交到地方官那里去接受审查,拒绝交出者就按私写反动言论惩处。
这往死里作践人的想法连乾隆都觉得过分,于是一个嘴巴又扇过去,把那走火入魔的海成打回了原形。其实乾隆私下里当然还是高兴,事情虽然做过了头,可奴才毕竟大体知道了如何少挨耳光的秘诀。
鲁迅曾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成了祸害是起于笑骂了清朝,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文字成祸往往更多是起于“隔膜”,这确是妙论。敢直接笑骂皇家的终是少数,但仅因隔膜而掉了脑袋才真真叫人恐惧。
而我以为,最恐怖的莫过于有意识地用精神自宫的方式去抹平隔膜的那种人,如海成之类。这厮知道了消除与皇上隔膜的方法犹如获得了做官的秘笈,但代价是必须摘净残存在身上的那点血性,宫里的太监只是去了男根,而奴才们的心理去势做得更狠,自己变态麻木,却还颇感怡然,如此一来,百姓可真没法活下去了。
我们总有个错觉,觉得清朝大一统有功,不管其手段是否恶劣,但总算把“北狄南蛮”统统攒和到了一块,至于人在里面是否活得窝囊好像已无所谓,为了大一统,那些个体血泪的牺牲仿佛都是应该的。可我以为,人的尊严不应因任何廉价或高尚的替代品出现而遭随意践踏,否则我们将会永远生活在乾隆淫威的阴影之下。
-------------------------------------------------------------------------------
这文章里面的“精神药渣”这词用得真令人拍案叫绝。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 ‘中医’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医学的最重要理由是,‘中医’总是呈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
杨念群:人的自由、尊严很重要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现在是维稳思维,外来势力越来越频繁地影响中国的治理格局,怎么样去笼络、维持住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格局?你必须要靠强制的国家力量对地方进行渗透,为什么现在一些个人的自由被剥夺,或者个人尊严受到伤害,都是以这样一个维稳或者维持国家一统的局面作为借口,这就是大一统格局付出的代价。包括我们历史上经常听到的号召也是这样,什么“为了我们民族的生存,为了对抗西方帝国主义,为了我们的国家统一,必须牺牲个人尊严,牺牲个人自由”。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找到相对平衡一点的理由呢?控制过严了,对人的自由、尊严都是有很大伤害的,这也是我所说的感到“郁闷”的原因之一。其实明代皇权对思想自由也有不小的伤害,并不是说只有清朝才面目狰狞,但是正是因为清代控制的太严了,文网太密了,才使人感觉尤其不舒服。
杨念群:科举是代议制,可惜被破坏了。秀才,皇帝是文化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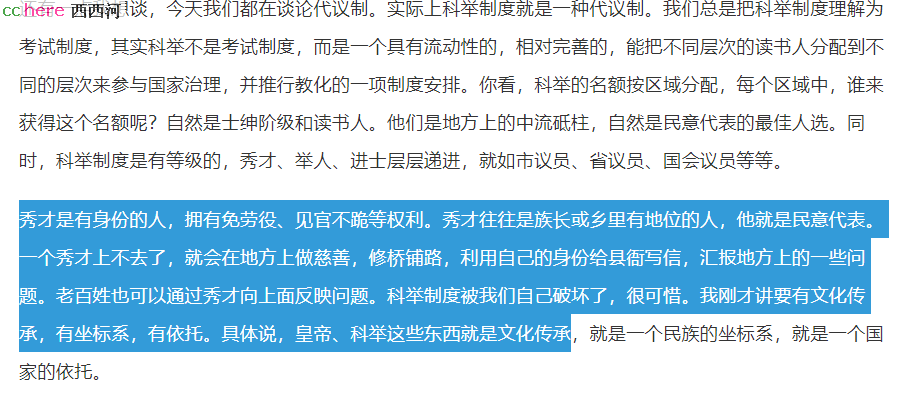
杨念群:最喜欢明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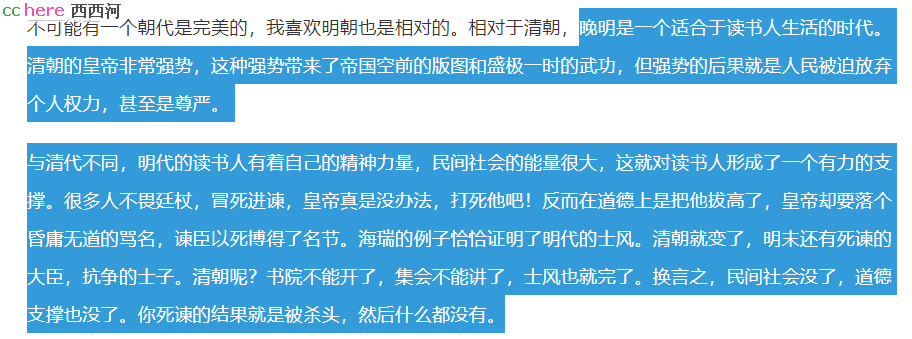
杨念群:皇帝的消失是一个损失,满人当皇帝正统性更强
我觉得皇帝消失对中国是个损失,应该保留皇帝,在保留皇帝基础上做什么都可以,搞民主、搞宪政……都行。“皇帝”首先是一个符号,为什么不让满清人做这个皇帝呢?革命党反满,从某种激扬慷慨的革命角度他是有理由的,但是另一方面,“皇帝”是一个文化符号,它凝聚的是多民族共同体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符号,当年乾隆既是大汗又是满人和汉人的皇帝,同时又是大喇嘛,它是凝聚多民族共同体的一个象征,不仅仅是一个皇位存留的问题。当然,是要汉人当皇帝还是满人当皇帝,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满人在大清的框架下它的合法性、正统性更强一些
喜欢用历史化的概念去讨论普遍……明知因为语境(预设)会有理解偏差。
比如他的秀才都是被后文定义的,而不是我们理解的秀才。秀才的确完成了这样的职能,甚至要掏许多钱帮人办事,组织公益。但问题是,乡愿显然更多。所以这里只是经过限定的理想情况,而未考虑制约和普遍形式。简单说,只能表露出某种当乡贤的向往。也许这就是目的所在?
还不如用钱穆的士人精神来说,那样就只是价值而不是特定事实了。不过也就没法突出制度了不是?
另外第一句是余岩明的话,还是近代西医视角,绕不过弯来。他这话的背景恰好和现在一样,是防疫,是群体预防和治疗上的不足。当时广谱抗生素什么都能治,中药却会因人而异,当然比不过人家了。只是现在的精准医学也可以说是分散面向病人个体,而中成药也在广泛应用……中药也在抗疫。
关于应不应该有一个皇帝这个问题,我个人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现在皇帝已经被打倒了,不可能再把皇帝请回来,我只是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历史语境、历史状态之下来考虑皇帝在当时、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那个时代的皇帝的作用和最后经过革命把皇帝推倒之后所造成的问题之间,我们应该有一个对照,也就是说,皇帝在不在或者皇帝有没有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把皇帝当做一个完全负面的、完全可以不用讨论的问题,好象只有打倒皇帝这一条路可以走,其它都是反动的想法,只有革命才是唯一最合法的道路,只有革命是最先进的,只有革命才是最彻底的变革之路。从这个角度我们应该重新把皇帝请回来,放在我们的面前重新审视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我所做的一个工作。举个例子,前年,关于辛亥革命有很多讨论,但是有关辛亥革命的讨论令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是一个现实政治工具而已,大家一味地对它歌功颂德。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纪念史学,每隔几年就大唱一遍颂歌,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意义已经毋庸讨论了,我们只是纪念它,对它高唱赞歌就够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好像是必然的,所有跟辛亥革命成功相违逆的东西都是反动的,都是不能讨论的,或者是都不需要讨论的,这是那一年开会的基调。去年我们清史研究所开始注意是否能换个角度对革命加以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把清帝逊位重新纳入到清末民初的历史框架中来,所以开了一个“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的研讨会,我开了句玩笑说我们要开一个“反革命”的会——当然不是真反革命,不是把自己真当成一个反革命去捍卫什么,那是遗老遗少的立场--为什么要开一个“反革命”的会?因为我们从来把革命看作是一个必然的、不用讨论的毋庸置疑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必须被质疑。革命并不是说不好,革命肯定有它的理由,但是革命并不能成为我们遮蔽或放弃讨论其他救国方案的一个理由,我们应该把当时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话题释放出来,跟革命进行对话。我们并不是完全否定革命,因为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已经摆在那儿了,但是辛亥革命意义阐释以外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被遮蔽掉的,根本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所以我们做历史研究的有责任把所有被遮蔽的东西重新请回来,中国是否应该保留皇帝只是其中的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之一。
在上海最近我们也有一个聚会,专门讨论立宪的问题,现在立宪不能公开谈,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是可以讨论的--有人说你怎么变成遗老遗少了。我自己并没有强烈的所谓名人情结,一定要为祖宗弘扬什么,好象祖宗说什么都是对的。我非常尊敬我的祖先,但不会变成盲目的崇拜者,我一定会把我的曾祖放在一个开放的格局和框架里进行审视,把各种因素纳入到这个框架里,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人说你就是遗老遗少,想把皇帝请回来不就是证明吗?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叫“文化保守主义”,我说我绝不是一个狭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我只是在这么一个开放的框架下,认为保留皇帝在那个特殊时代是有必要的。当然,您说的刚才那点我也同意,皇帝未必凝聚了所有传统资源,满人的汉化程度可能也很严重,晚清早已不是那个满人的皇帝了,但是我觉得他恰恰因为不仅仅是满人的皇帝,所以他身上具备了一种凝聚不同民族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他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象征符号,但是我觉得如果保留着这个符号,中国所有的改革和开放的设计可能比现在稍微要更合理一点。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往往并不一定是皇帝一个因素导致的,但是民初变革遭受挫折肯定跟皇帝不在有一定的关系。这里我还是要反复澄清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不是一个保皇派,我只是在现有的框架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讨论。
人民不具备皇帝这样凝聚人心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向大家请教。大家都在谈中国立宪的问题,当然现在表面上中央不让谈,“七个不准”。我想从历史上,我仅仅从历史上来看,立宪和代议制有关,和整个民主选举制度有关。在满清那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大家现在一直在讨论。经过革命以后,整个民主的主体发生变化了。按照当时梁启超和杨度先生的设想,如果保留皇帝的话,在底下可以展开很多民主制度架构的建设,如果把皇帝推翻的话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把皇帝推翻以后用什么来替代那种象征意义上的文化符号?人民?什么是人民,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各个阶层都可以叫人民,但是人民具备有一种像皇帝这样凝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象征意义上的作用吗?目前看来人民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作用,因为到现在为止人民的内涵和边界不断地在移动,所以人民到底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可以掌权?如果人民不能直接掌权,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掌权?谁能够代表人民掌权?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中所聚焦的代议制的作用问题。如何实现代议制?通过直接选举吗?或者有什么其它可靠的选举方式可供选择吗?现在大家也讨论得非常激烈,有人觉得选举也不是一个解决民主变革问题的好方案。我自己有一个想法:如果从我们杨度先生那一代开始,大家都意识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把传统制度摧毁之后,有些东西是无法挽回的,也许我们已经丧失了传统遗留下来的一些很好的制度,把它们当作糟粕给清算掉了。比如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说,中国最好的代议制实际是科举制度。大家都把科举制度仅仅狭窄地看作是一个考试制度,从晚清开始就把科举制度骂得很惨,说它就是八股文,使人头脑僵化,摧残人性等等,但是科举制度其实和现在的高考制度有密切的关联性,现代高考制度基本沿袭了科举制度按地区进行名额分配的原则,因为科举制度是最讲名额分配的。最繁华的地区比如江浙地区考中科举的人非常多,所以皇帝就有意限制这个地区的名额,他会照顾边疆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行省,名额分配要往这些地区倾斜,造成相对均衡的态势,尽量使更多地区的士子都能得到晋升的机会。因此,科举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一种代议的特点,因为它的名额分配相对比较公平。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个地区绝对平等,但是因为名额分配相对均匀,所以在机会平等上,科举制度创造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局面,这是第一点。
第二,科举制度为什么具有代议的性质?科举制度把人才均匀分配在不同的层次和地点,这是现在我们任何制度所达不到的,所以科举制度的废除我觉得太可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在科举制度下,你考中了进士,可以进翰林院,可以当大学士;考中了举人,就只能当县长,不能再往上爬了。如果你连举人都考不中,就是个秀才,你就只能待在村子里。但是秀才在地方上有一点特权,比如可以免劳役,交税的额度也可能较低,这是非常大的优惠,但你必须为乡里服务,比如要从事一些社会救助活动,有时还要为老百姓代言。这个制度还使得人材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秀才也可能过两年考中举人了,就可以当县官了。如果当县官还觉得不满足,再考几年,考到六十岁,弄不好就成了进士,变成皇帝的幕僚了,说不定也可以当上清朝的军机大臣。因此它是不断流动的。如果秀才考了几十年,皓首穷经也考不上,就老老实实地在乡下待着,修桥铺路,发展教育,做一切有利于乡梓乡邻的事情。很多宗族的族长就是由秀才来承担的,因为只有他最有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举人、秀才和进士的梯级分配非常均匀,我觉得这就是代议制,因为秀才在基层就代表了民众基本利益,他往往承担着推动本地区文化教育、慈善救济和公益事业的责任,他要为民众负责,而且有时候就是族长,人们有什么诉求都会优先求助于秀才。
科举制度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代议制度,而且它是上下流动的。我们把它破坏掉之后,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替代它的新式学堂根本不具备它的功能。新式学堂是培养专门人才的,也就是培养技术人才的地方,出来后大多是行政技术官僚。新式学堂的人虽然学了满脑子技术知识,后来却往往被认为是没什么文化的:第一,因为缺少道德训练。你看当时学堂的学分设计,道德课被缩减到一两个小时,传统文献、传统经典不读了,学生基本蜕化为一个技术人员;第二,因为没有科举制度对人员分配的上下层和地区的限制机制起作用,进了学堂之后的学生不用回乡,不用回村,大多数就直接进城了,进城之后谁也不愿意回到乡村服务。现在高考制度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清末及以后,我们知道,学堂教育之后的最佳出路都是留学,这条道路培养了一批理工男,一批没有文科基础和传统文化训练的人。这套机制把科举制上下流动的循环系统完全破坏掉了,我觉得这是清末一个最大的损失。清末新政把科举废除之后,教育本身的那种教化和政治相互辅助的关系被完全割裂了,基层管理人员的文化水平就衰落了很多,基本上培养的都是技术官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不一定对,我觉得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是知识分子,我要政治地位。
我最喜欢明末,我最喜欢宋朝。口口声声说原因是:要自由。
元朝也很自由,他为什么不去元朝,不就是觉得明末,宋朝。知识分子有政治地位吗?
自由值几个钱,没有政治地位都是空的,人家杨教授的历史一点也没白学。
明朝亡了又怎么样?我一个知识分子摇身一变就能去清朝当官。钱谦益不是说水太凉吗?转身就去清朝当大官,回头清朝收税收到自己头上,又去暗通反清势力。变来变去,唯一不变就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不能降。
人民算什么,有我知识分子重要吗?国家算什么?只要政治待遇给够,什么汉奸都能当。
要皇帝,要科举制,要这个要那个,千言万语就一句话,我要政治待遇。
你说话也不要绕来绕去,好的没学会,学会不说人话了。想说什么就直接说,没看有多少见识,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倒一大堆。
你要是跟他较真,他完全可以搬出自己的话是历史学的定义,不是你想的那样,而且他的结论是被实证史学所认可的。也就是故意混淆。就像四库帖子,无论混淆什么,单单「他想混淆」就足够可恶了。
不讨论这点当然很简单,就是想当土司乡贤。
中医那段话更简单——概念不对等。中医被限定,西医被扩充。但是不解释恐怕不容易被认可,也可能是最近和车轱辘话解释太多成习惯。要知道货币的帖子,只一两句人家就懂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就是传统中国的边界,最多初中知识水平就能理解。说中国边界不清,是不对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哪来什么疑问?
我赞成你“讳疾忌医”的说法,是认为历史应该什么都可以谈,没什么好忌讳,比如清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以谈;摊丁入亩仕绅一体可以谈;剃发留头可以谈,平判准噶尔也可以谈。谈的目的是总结经验,总结经验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和平富强。如果蒙满曾跟汉族战争过,就把他们驱逐出去,那么哪个民族没跟汉族干过仗?都赶?汉族也曾不止一次分裂出地方势力,怎么赶?谁赶谁?
某些人的言论,算什么?就那么有代表性和真理?一个事,说啥都有,什么才是正确的?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才是正确的。
至于元清非中国说,新清史之类的,日本之流的有没有起到重要作用?说没有估计没人信吧。